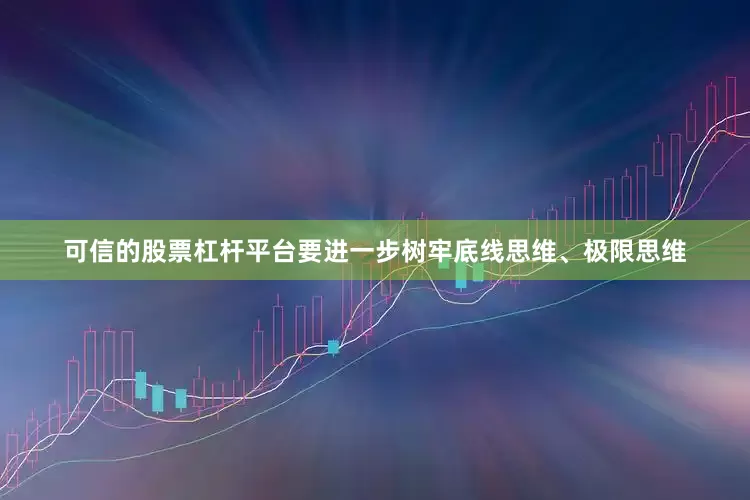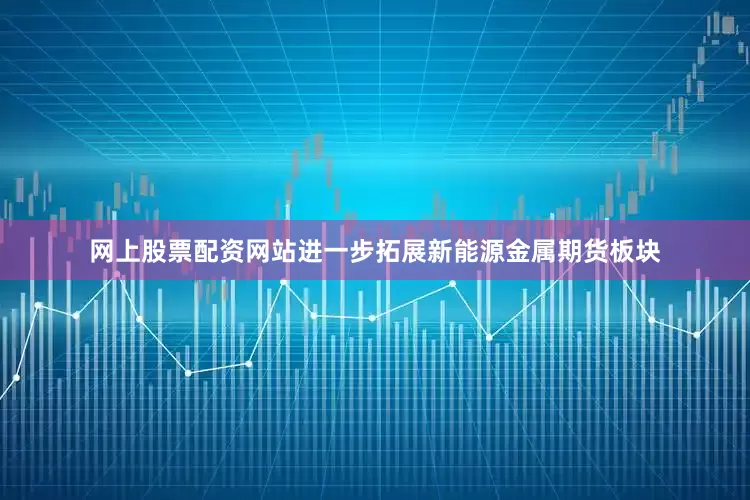朝鲜战争中的中国朝鲜族:4万人奔赴前线,1万余人为何选择回归东北?

1950年初夏,鸭绿江畔的晨雾还没散尽,一队队身着解放军制服、口音里夹杂着东北味和朝鲜语的年轻人,正整装待发。他们大多来自吉林延边、黑龙江五常或辽宁丹东,是中国境内最早一批“移民二代”——朝鲜族。彼时,这些士兵即将跨过国界线,从沈阳、长春等地直奔战火未熄的邻国。四万多人出发,却只有一万余人最终踏上返乡路。这背后,有血有泪,也有难以言说的人生选择。

如果把时间拨回19世纪末,中国东北还是大片荒原。那会儿,大清边防松垮,加上甲午战争后局势动荡,不少来自朝鲜半岛北部的农户,为了逃避饥荒和殖民统治,只能背井离乡。他们带着水稻种子,在松花江流域扎下根来。这群移民后来成了中国官方认定的“朝鲜族”,也是新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独特的一支。

抗日战争时期,日本对满洲实行高压政策,不光本地汉族遭殃,连这些刚安顿下来的外来户也难逃其害。“改名换姓”“强制劳工”,还有不少青壮年被征去修铁路挖矿。面对双重压迫,有胆大的就加入了抗联或者地下党组织。据《东北抗日联军志》记载,仅在延吉地区,就活跃过十几支由朝鲜族青年组成的小分队,他们夜里袭击伪警察所,白天帮村里老百姓藏粮食。有个叫金昌德的小伙,还因为救下被捕同伴,被誉为“延边小诸葛”。

1945年日本投降,这些武装力量没有解散,而是顺势并入了解放区的新秩序。在辽沈战役期间,据第四野战军档案记载,仅164师一个团,就有近三分之一是会讲两种语言的老兵,他们既能当侦查员,又方便与苏联红军沟通。一时间,“会说话”的士兵成了香饽饽。

1949年,中共中央收到金日成方面请求,希望把驻在东北的大批精锐调往新成立不久的邻国,以充实人民军骨干。当时,新中国刚立足脚跟,各类资源都紧张,但考虑到国际形势以及民族情感,北京拍板同意这项特殊转移。据《中共党史资料通讯》披露,当年的调遣规模空前,两个月内就完成两万人编组,还给配备了步枪、机枪甚至迫击炮,比起普通新兵可阔气多了。

这些部队到了平壤,很快被编进第5、第6、第12师等主力序列。从美方公布缴获文件来看,那几年人民军里的中文笔迹作战命令屡见不鮮,美方情报人员还专门研究过“中国籍韩裔官兵”的心理状态。不夸张地说,在1950年前半年南北拉锯阶段,这批从松花江走出来的小伙子,就是金日成手头最靠谱的一股力量。

但好景没持续太久。仁川登陆后局面急转直下,第6师在马山损失惨重,第5、第12师更是在洛东江防线上伤亡极大。《联合国军事委员会报告》中提到,仅1950年底三个月间,被俘或阵亡人数接近总数一半以上。而且,由于他们多数不会完全适应当地生活方式,与本土官兵之间偶尔也出现隔阂,比如吃饭习惯、休假方式都闹出过小摩擦。有学者分析,这种文化差异无形中加剧了一部分人的思乡之情——毕竟谁家灶台不是自家的烟火香?
到了停战谈判尾声,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面临人生抉择:留在满目疮痍的新国家?还是返回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大院落?据1982年《黑龙江省志·人口卷》统计,当时仅五常县登记在册归国老兵209人,多数已重新务农,还有少量进厂做工或参与地方建设项目。他们回来之后,并没有像想象那样受歧视,相反,由于具备丰富军事经验和组织能力,经常成为村里的生产骨干甚至基层干部。一位名叫李春植(化名)的老人曾回忆:“我小时候天天盼爸妈回来,一听打仗结束就跑去车站守着。”

政策层面也很给力,新政权明确规定只要1949年前就在国内居住,无论有没有拿到正式证件,都按本地公民对待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的出台,更让他们享受到用母语教学、自办节庆活动等权利。在延吉市档案馆还能找到1957年的一份文件,上头盖章批准某小学设立双语班级。当年的孩子,如今很多已经退休,却依然能用流利汉语聊起当初父辈从鸭绿江彼岸归来的故事。

至于那些没选返程的人,其实原因各异。有的是因为亲属已全部迁徙至半岛南北,无牵挂;有的是觉得自己作为劳动党成员,更适合留守;还有极少数因伤残无法远行,只得安身现地。不过据韩国学者朴永哲统计,即便如此,到1981年前后仍约6000人在世,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体系。不管怎样,每个人心底都有段属于自己的历史剪影——有人怀念家乡炊烟,有人珍惜眼前土地,但无论在哪,都得继续活下去,把苦辣酸甜咽进肚子里再慢慢消化掉。

今天,如果你走进吉林珲春某个村庄,说不定还能碰上一位拄拐杖遛弯儿的大爷,他操着带点口音的话告诉你:“我们那时候,可真不是电视剧演得那么简单。”他的孙女可能正在手机上刷短视频,看见关于70多年前那场战争的视频弹幕密密麻麻,然后抬头问一句:“爷爷,你是不是也打过仗?”历史,就是这样穿梭在人间烟火与冷风交错之间,不知疲倦,也永远不会彻底尘封起来吧?

内容来自公开资料与个人见解,仅供学习交流,不构成定论或权威史实参考。

景盛网-线上正规配资-网络配资门户-股票杠杆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