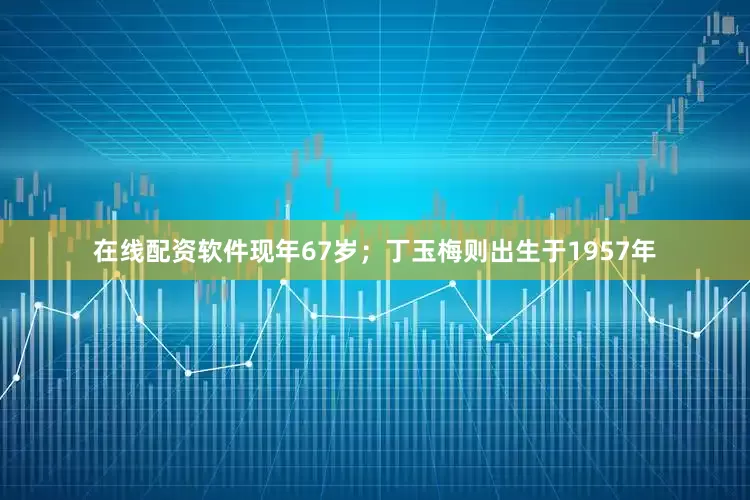毛主席三请不动她,副部长不当非要去教书,这老太太到底图啥?
1977年,北京的冬天来得特别早,冷风跟刀子似的。中南海旁边那条小路上,一个瘦得像张纸片的老太太,裹着件洗得发白的旧呢子大衣,走得颤颤巍巍。
她叫王一知。就在刚才,教育部会议室里一众领导干部,客客气气地请她出山,担当要职。她呢,就那么轻轻巧巧地回了句:“我只想教书。”

这已经是第三回了。从新中国一成立,那些跟她一块儿从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老战友,像毛主席、周总理,变着法儿地想把她请进中央。可每一次,她都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,转身就回了学校。
一个在地下战线潜伏了几十年,连毛主席都开玩笑说“你该到地上来透透气了”的传奇人物,怎么就跟三尺讲台死磕上了?这事儿,咱们得把时光倒回去,从头捋一捋。

1901年,王一知生在湖南芷江。她那个爹,虽说是留过洋的,可脑子里那套重男轻女的旧思想,比老宅的墙砖还硬。母亲走得早,她在这个家里就成了多余的人。
14岁那年,这姑娘揣着几件破衣裳,硬是靠自己考进了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。学费怎么办?给人打杂、教小孩识字、在食堂帮工刷碗,什么苦活累活都干。

苦日子没把她压垮,反倒把她的骨头淬炼得比钢还硬。1919年,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,长沙街头,一个剪着短发、领着几十个女同学高喊口号的姑娘,格外扎眼,那就是她。带头抵制日货,闹得满城风雨。
在那个年代,一个女学生敢这么折腾,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可她眼睛里的那股劲儿,比啥都亮。也正是这个时候,一颗种子在她心里悄悄发了芽——教育救国。

后来,她去了向警予创办的溆浦小学教书。站在讲台上,看着底下那一双双清澈又渴望知识的眼睛,她头一次感觉到,心里头那种踏实感,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。
可惜,乱世容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。1922年,她到了上海平民女校,在这里,经刘少奇介绍,她成了一名共产党员,也认识了陈独秀、张太雷这些后来响当当的人物。

1925年,她和张太雷走到了一起。没婚礼,没仪式,俩人就一句话的事儿:“从今往后,并肩作战。”白天俩人凑一块儿写传单,晚上一个往东一个往西,分头去送情报。那间小破屋里,装满了比蜜还甜的理想。
好景不长,1927年,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,年仅29岁。他是我党早期牺牲的最高级别领导人之一,当时他们的儿子才刚满月。王一知没掉一滴眼泪,抱着孩子,咬着牙继续干地下工作。她说:“眼泪,那是留给敌人的。”

后来,周恩来亲自给她下任务,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。那可是当时党中央的“千里眼”和“顺风耳”。她愣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,同时运转三部电台,情报像水一样,源源不断地流向延安。大家看过的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,主角李白的原型,就是她领导下的电台报务员。
1942年,李白电台暴露,情况万分危急。她一边冷静地安排同志们撤离,一边自己抱着党组织的全部经费,在特务的搜捕网里钻来钻去,硬是没让一分钱落到敌人手里。这份胆识和能力,让所有人都对她刮目相看。

所以啊,新中国成立后,老领导们都惦记着她。第一次请她出山,毛主席还跟她开玩笑:“一知同志,你在‘地下’待了这么多年,也该到‘地上’来工作啦!”
可王一知心里跟明镜似的,她知道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。在战火里,她都没放下过教书这件事,在合江女中任教的日子,让她越发坚信:一个国家想真正站起来,得靠年轻人。年轻人的腰杆子硬不硬,就看教育的根扎得深不深。

1949年,她主动请缨,去了上海吴淞中学当校长。那学校,被炮火轰得就剩下半拉楼,教室里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找不出来。她二话不说,卷起袖子就带着老师学生们一起搬砖头、修房子,累得整个人都脱了相。
学校里有些留用下来的老教师,作风散漫,有人就建议,得狠狠批一批。王一知摆摆手,说:“教育这东西,不是靠骂人能搞好的。”她每天第一个到校,带着大家一起备课,跟老教师们坐下来谈心,聊新教材。慢慢地,那些原本心里有疙瘩的人,也都心悦诚服地站上了讲台。就这么一年多,一个“破烂学校”硬是被她办成了上海的重点。

1954年,中央第二次下调令,请她到教育部任职,给的是行政八级待遇,说白了,就是副部长级别。她又给拒了,转头去了北京,接手了华北中学。这学校有点特殊,建在圆明园的废墟上,只收干部子弟。她一看孩子们身上那股子优越感,心里就咯噔一下。
第二年,她力排众议,坚持把学校改成面向所有普通家庭的子弟学校,还给学校取了个新名字:“一〇一中学”。她跟老师们解释:“过去就算是一百分,咱们现在也要从一开始,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。”这名字,也寄托着在一个民族耻辱的废墟上,培养出超越前人的下一代的期望。
为了磨掉孩子们身上的娇气,她带着学生在废墟上开荒种地、修操场,甚至自己掏钱买设备建校办工厂,搞半工半读。她还主动申请,把自己的行政级别从八级降到十二级,她说,只有跟基层老师一个待遇,才能摸到教育真正的脉搏。
时间一晃到了1977年,国家百废待兴,中央第三次派人来请她。这次的理由更充分:国家要改革,需要您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同志,来参与顶层设计。
可这位76岁的老太太,还是回到了她的一〇一中学,继续给学生改作业,带孩子们下地劳动。她说:“教育不是站在高处喊口号,是弯下腰,握着粉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写。”
在她当校长的三十年里,从她手底下走出去的学生,成了各行各业的顶梁柱。写出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的音乐家施光南,主持制定《体育法》的伍绍祖,还有后来参与国家工业改革的李铁映……
1991年,90岁的王一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遗言很简单:“不要开追悼会,浪费大家时间。”可追悼会那天,八宝山里里外外挤满了人,有穿军装的将军,有戴眼镜的学者,有拿画笔的艺术家,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王校长的学生。他们排着长长的队,就为了再送自己的校长最后一程。
你说她傻吗?放着副部长的高位不要,偏要去守着那个清贫的讲台。
其实,她比谁都活得明白。那些年在地下战线,躲过的一次次枪林弹雨,为的不是自己将来能坐多高的位置,而是为了一个能让孩子们安安稳稳读书的新中国。她那三次转身,拒绝的不是权力,而是选择了一条她认为能让这个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根本道路。她不是不想“到地上来”,只是在她心里,最坚实、最广阔的“地上”,永远是那三尺讲台。
景盛网-线上正规配资-网络配资门户-股票杠杆网站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